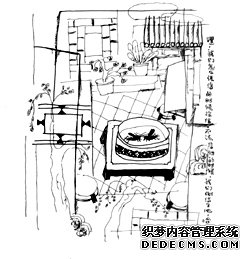
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,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这帮孩子的注意。首先,这院儿里的名人就够多的了。而美术界的名人和这院儿里的孩子都个个面熟。
远了我也不和你说,就说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先生,和这个院儿的关系就千丝万缕。齐爷爷一来,全院儿的孩子就前呼后拥跑来看,虽然人们都知道,齐老先生由于特殊的处境,脾气比较特别。比如:到齐爷爷家千万不要吃他给你端出来的月饼和花生,你要真动手就等着回家挨揍吧。一来你真吃了,齐爷爷肯定心里不高兴,二来,你肚子肯定要出问题,那月饼和花生都不知是猴年马月保留到如今的。
但是,他对孩子们都是一样地和蔼可亲,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每人就是一块钱,那年头对孩子们说来那就是一笔巨款了。我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倔强的老头儿,虽然那时候,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画到底有多么好。
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,他才28岁。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45岁,董希文先生那年也才38岁,我爸才35岁。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53岁了,可是今天来看,都这么年轻啊。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大雅宝的这个院儿,真是个艺术大磁铁,各种年龄的各路豪杰都被吸引到一起来了。
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一个中国人,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。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,挂在肩膀上似乎只有两根带子。裙子上面还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。20世纪50年代北京就没见过有人这么穿过,甚至也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。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,显得相当清爽。
和黄叔叔斗蛐蛐儿,是我们和他深交的开始。
暑假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斗蛐蛐儿。黄叔叔也有绝的,他对我们说:他自己逮蛐蛐儿早就是多年的行家高手。让我们全力以赴,好好去逮,回来以后才有资格去找他斗蛐蛐儿,大战三百回合。
经过我们几天的认真准备,我和沙贝、李燕、小宝也进行了演习性的战斗,最后选出来三个最厉害的蛐蛐儿,就相约一起到黄叔叔那里去比个高低。我们一人捧住一个罐儿往前走,后面跟上了全伙梁山好汉。
黄叔叔把他们家的小炕桌四平八稳地放在院子中间,再转身回去,像魔术师一样,接二连三捧出了几个大号澄浆底的专业蛐蛐儿罐儿。
一看他的罐儿,我们全有点儿犯晕,他还真是玩真的。这等级的罐儿我们也就在东四牌楼旁边隆福寺的蛐蛐儿市上见过,我们这胡同还没人玩到这一级别的。这些老罐儿又大又沉,价钱我们从来没敢估。
他“嗡”的一声打开蛐蛐儿罐儿的盖子,余音袅袅,和打镲一样。哈,难怪有人管这种罐儿叫钢罐儿呢。他这一“嗡”绝对是一种金属才能发出的声音。
我们伸头望去,还看不见蛐蛐儿,罐儿里面镜面一样黄色澄浆底上,一个小巧青花瓷过笼。他轻轻捏开过笼的顶盖儿,那蛐蛐儿在家呢。那蛐蛐儿没有八厘,也得七厘五。不但个儿大,还全须全尾全大夯。所谓大夯就是它的大腿,浑身油亮油亮的。大黑头点了漆似的锃光瓦亮,那水牙就显得格外洁白。那紧拢的双翅,隐隐透出一层金光。黄叔叔用他号称用耗子须做的蛐蛐儿探子,轻轻一扫,它立马开牙,双翅一抖,“喳喳”叫了起来,还有节奏地颤动着大腿,似乎在继续挑战示威。
“哇!”我们几个当时都傻眼了,我们这帮“土匪”在大雅宝的蛐蛐儿沙场也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主儿了,今天才又真正开了眼。这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比赛,我们就和中国足球队进了世界杯32强一样,不赛不知道,一赛吓一跳。不用细说你也知道,我们的几场比赛,一共就是四个字:落花流水。
最多一两个回合,我们的蛐蛐儿只有逃跑的份儿了,还有一次还是我们的一号选手,更让黄叔叔的大将军愣给甩出了罐儿。
我们本想镇黄叔叔一把,没想到是他把我们全彻底地反镇了一把。
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他的几个大将军的名字绝不那么俗气,不是叫大红袍、大青翅之类的。他一号大将的名字叫寥寥,啊?那是我弟弟的名字啊。他解释说:这个蛐蛐儿叫声厚重,寥寥是个粗喉咙,所以起了这个名字。
二号是叫得清脆,所以它就叫小仔儿。哈,那是詹先生儿子的名字,因为他哭声嘹亮。三号是个大哑翅,于是就叫小弟。那就是李可染伯伯的小儿子李庚啊。李庚是沙喉咙。他的外号麒麟童,也是黄叔叔给起的。好,他的蛐蛐儿全借用我们院儿小一帮孩子的名字。
我们笑得前俯后仰,沙贝赶紧问:你的蛐蛐儿到底是从哪儿逮的?
黄叔叔一本正经告诉我们说,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后面的小山上。啊?我们怎么没想到那里会有这么好的蛐蛐儿呀?等我们马不停蹄地跑到中央美术学院后面的小山上,狼烟四起把小山翻个底儿朝天,别说八厘的蛐蛐儿,就连个蛐蛐儿秧子也没见着。
嘿!我们怎么该信他的时候没信,不该信他的时候,我们倒信了他。哈!
(作者:张郎郎)
乐清上班族_微信公众号

乐音清和_微信公众号

有声杂志_微信公众号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