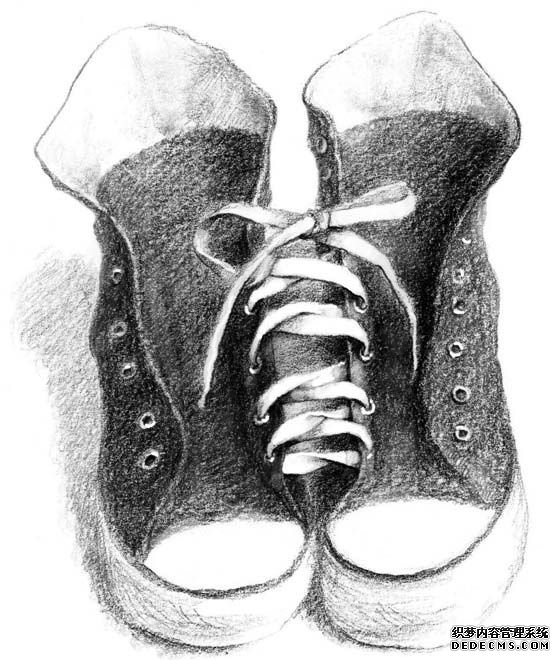
2003年,伊朗的一对连体姐妹决心通过分离手术拥有各自独立的人生,但手术失败,姐妹二人也因此离世。这个悲剧给了加拿大女作家罗莉·兰森灵感。2005年以一对连体双胞胎为主角的小说《那两个女孩》一经出版,便获得《纽约时报》《华尔街日报》年度小说推荐;它入围了2007年柑橘文学奖,被翻译成18种文字在全球出版。本刊摘选其中一节——
我从未直视过我妹妹的双眼,从未独自一人沐浴,从未站在夜间的草丛中伸出双臂拥抱那醉人的月色。我从未用过飞机上的卫生间,从未戴过帽子,或是被人深情地亲吻。我从未开过车,或是一觉睡到天明。我从来没和人说过私密的悄悄话,没有自己散过步。我从没爬过树,甚至从未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。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未做过,可是啊,我却被给予了如此多的爱!而且,即使让我能够做这些事情,我也宁愿如我现在这样再活一千次,只为获得这无限的爱。
我的妹妹露比和我,本应从一个单体受精卵分裂开来,不知是不幸还是奇迹使然,我们竟依旧连在一起,因此,我们便成了一对颅部连体的女婴,连体部位有面包盘大小。我们作为存活最久的颅部连体双胞胎(我们已经29岁了)被世界医学界所熟知。我们被人们冠以诸多名称:畸形、怪人、怪物、魔鬼、巫婆、弱智、奇观、奇迹等等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我们算是一件珍奇异物,但在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利福德小镇上,我们只是“那两个女孩”。
伸出你的右手,用手掌根压住你的右耳垂,使手掌盖住右耳,然后五指伸开——那便是我妹妹与我的连体之处。我们的脸不是完全并行的,我们的头骨融合在一起,连体部位是一个从太阳穴开始延伸至前额叶的圆形区域。要是你看到我们,你可能以为我们是两个拥抱在一起、彼此脑袋相靠的女人,亲密得就像一个人。
露比和我是一对同卵双胞胎,所以有着相同的样貌,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有着高高的额头,嘴巴宽而丰满,只是露比的五官出落得更端庄(实际上,露比长得美极了)。我们的头皮在二人头部相连处长在一起,但我是一头赭石色的卷发,我妹妹则是一头深褐色的飘逸长发。露比的下巴上有处深深的凹陷,十分讨人喜欢。
我身高五英尺五英寸(约1.65米)。我们出生时,我的四肢匀称,身体比例协调。而现在,我的右腿比左腿足足短了三英寸,我的脊椎被压迫得厉害,我的右臀隆起,这都是因为从我自己还是一个婴儿时起,我就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我妹妹。露比两条细小的大腿跨在我臀部上面的部位,我的右臂支撑着她的臀部,她的胳膊一直缠绕着我的脖子。露比是我的妹妹,听起来奇怪却无法否认的是,她也是我的孩子。
连体双胞胎总会有一些不便之处。露比和我要经历颈部、下巴和肩膀部位的疼痛,或轻微或剧烈,为此我们每周要接受三次物理治疗。我一直身有重负,因为我要承受露比的体重,我要用臀部背负露比的身躯,躺着时我要挣扎着为露比翻身,还要在马桶边的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(露比身患各种肠道和泌尿系统疾病)。毫无疑问,我们时时都在面临考验,经常会遇到不适,但露比和我从来都不觉得躯体相连让我们感到痛苦。
很难解释身为连体双胞胎的我们是如何协调行动,或是如何自出生时起,通过咕哝和手势磨合出一套我们二人称之为“心灵感应”的东西的。和正常人一样,有时候我们也会笨手笨脚,毫无默契。当我们中的一人(通常是露比)生病时,我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出问题,但大部分情形下,我们的“双人舞”可谓顺畅自如。我们讨厌做事行动一致,比如同时回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。我们从不接替对方把话讲完。我们不能同时摇头或点头(即使我们能也不会这么做)。我们有一套不需言传,甚至是无意识的制衡体系来决定谁在某一特定时间来带路。有冲突,也有妥协。
露比和我共享一个血液供给系统。如同我们的头骨一样,我们共享着一个大约由一百条静脉组成的血管网络。我们的脑组织完全融为一体,我们的血管系统如疯长的荆棘般彼此缠结,但我们的大脑却各自分开,独立运转。我们有各自的想法,我们各自拼命想要变得独一无二,不同于对方。事实上,我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大多数同卵双胞胎都大。我喜爱运动,也爱看书,但露比更女孩子气,她喜爱看电视。露比感到疲劳想要睡觉时,我还完全没有一点儿上床睡觉的打算呢。我们很少同时感到饥饿,而且我们的口味偏好也截然不同:我偏爱辣味,可我妹妹对蛋的喜爱简直让人受不了。
露比相信上帝,也相信各种鬼魂和灵魂转世的存在(露比从不推测她下辈子的转世是什么样子,似乎想象成为任何与现在的她不同的人都会背叛我们俩一样)。而我则相信,对于死者而言,最好的希冀便是通过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或是书里的一个篇章,时不时地被人们回忆和缅怀。
我从未看过我妹妹,除了在镜子和照片中,但是从她肌肉和骨骼的一举一动中我知道,露比的姿态也是我的姿态。我爱我的妹妹如同我爱自己,我恨她时,也是在恨我自己。
这便是我的人生故事,我称之为《一对连体双胞胎的自传》。不过,我妹妹声称,她反对由我一人来讲述一些在她看来是属于“我们”的故事。
关于写作,我主要是从阅读和洛薇阿姨那里学到的。洛薇阿姨和斯塔什叔叔自露比与我出生起便抚养我们至长大成人。我继承了洛薇阿姨对阅读的热爱,尽管我很乐意认为我的生母也是个爱书之人。洛薇阿姨几乎总是书不离手。我们居住的老农舍后面是食物储藏室,洛薇阿姨在旁边的一间日光室里塞满了书籍。
从我们3岁起,洛薇阿姨就不厌其烦地对我们做严格的身体训练,对我们的哭声充耳不闻。一个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也许会认为,她有时对我们过于残忍了,但我知道,洛薇阿姨不仅仅是想要我们存活下来。她让我明白,露比永远在我一旁,我是“我”自己,我也是“我们”。
露比和我9岁时,洛薇阿姨开车带我们去利福德图书馆寻找有关连体婴儿的书籍。露比小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晕动症,现在也毫无改观。每次我们外出,哪怕路程很短,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她都在晕车呕吐,有时甚至吐得非常严重。露比的晕动症使我们早已严重受限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。
在去利福德图书馆的途中,露比呕吐了两次,等我们到达时,我身上穿的是我携带的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。
我翻开一本小红书,里面没有图片,但其中一个故事却像音乐一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英国威尔士的米妮和玛丽,二人自1959年出生时起便胸部相连(术语叫作胸壁连体儿)。到18个月大时,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比在外面还多。米妮和玛丽长得美丽极了,有着白瓷般的皮肤和浓密乌黑的卷发。她们笑的时候多,哭的时候少。二人经常彼此拥抱亲吻,但有时也会凶狠地打起架来,甚至需要护士制止才会罢休。她们的语言能力发育得很慢,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丝毫不受影响。出于某些原因,她们都称彼此为“玛丽”,可两人都把这个名字念成“Me”。于是,喜爱她们的护士和医生也都称她们为“Me”。米妮和玛丽的身体与正常人无异,只是二人共用一个心脏。但在她们两岁生日前夕,她们的心脏开始衰竭。
各科医师前来会诊,从胸外科、血液科到心脏外科,所有的专家都建议牺牲掉相对孱弱的玛丽,把完整的心脏留给更加健壮的米妮。时间已经所剩不多,医生们一再警告,如果不尽快手术,两个孩子都会死去。面对这些,孩子的母亲惊慌失措,便同意了手术的建议。她亲吻玛丽作为最后的告别,同时心中祈祷共用的心脏能让米妮活下来。米妮确实活了下来,情况甚至好过医生们最乐观的预测。手术后过了数天,当小米妮终于睁开眼睛时,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。连小米妮也被感染,跟着拍起手来,随后她习惯性地伸出胳膊拥抱她的姐妹,却惊恐又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孪生姐妹不见了。米妮环视整个房间寻找玛丽的脸庞。“Me?”她低声问道。医生和护士随即陷入一片沉默。米妮再次环视四周。“Me?”她哀求道,“Me?”这时,她向下看去,突然间,她似乎明白了,她的姐妹已经从自己的胸前被割除了。“疼。”她低声哭诉着,摸了摸伤口处的白色绷带。她的眼睛遇上了母亲此时早已泪水奔涌的双眼。“Me。”米妮又念了一次,便闭上双眼,也死去了。
洛薇阿姨很早以前便要我无所畏惧地书写我的故事,讲述我的真实生活,描绘我的理想人生,不仅仅是一个连体儿的故事,而是作为一个人,一个女人的故事。过了这么多年,这也是我将要做的事。“写下来,”洛薇阿姨说,“就当你的故事永远不会被人阅读。那样你一定可以讲出真话。”可是,我真的希望有人能读到我写下的故事。我想讲述我人生的真实故事——对着你讲述。
(左岸听涛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《那两个女孩》一书,王 青图)
乐清上班族_微信公众号

乐音清和_微信公众号

有声杂志_微信公众号

